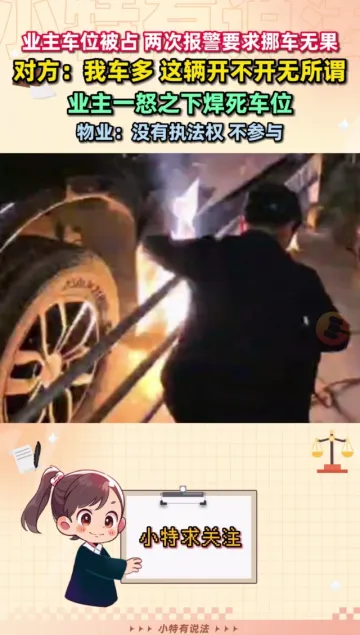下午一点,工业区路上行人不多,我经常与一只气定神闲的白鹡鸰不期而遇,它漫不经心地打量着我,我也朝它瞧了瞧,似曾相识。它对我的生分总是不多也不少,始终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,小脑袋忽左忽右,小小的喙在水泥地上快速地啄食什么。它惯常会向我展示它的翅膀,在低空盘旋,灵活地改变飞行轨迹,轻逸地掠过一株正在吐蕊的黄桷兰,消失在厂房上面。前人说它“飞鸣行摇”,它行走的时候虽然尾巴上下摇晃,但惯常并不卖弄它的歌喉,飞翔时也默不作声。也许白鹡鸰的“唧呤之歌”只献给同气相求的同类。
我有时有一种类似济慈之于夜莺的错觉,把我前天邂逅和今天遇见的鹡鸰看成是同一只。如果有可能,我并不想以“一只鹡鸰”来指代它,我们既然能够给一条河流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,何妨也给遇见的每一只鸟儿取一个美好的名字?!
开元七年的秋天,成百上千只鹡鸰飞到麟德殿的树上,盘桓数日都不肯离去。看到这么多鸟儿翔集,连生活在深宫里的李隆基也觉得不可思议,他触景生情想起自己的一帮兄弟来,暌违已久,他们的形象在脑海里似乎变得不那么真切了。对普通人来说,兄弟之间的推枣让梨算不得什么,但生在帝王家,兄弟友于大抵只是一个美好得一触即破的泡影,至高无上的皇权是世间最狠的毒药,总把亲情杀得一片落花流水,什么手足之情先关进笼子再说。此时李隆基的五个兄弟都在外地各守其职,一年难得一见。小时候,兄弟们一起朗诵《诗经·小雅·常棣》:“脊令在原,兄弟急难。每有良朋,况也永叹”,往日的情景历历在目,书声似乎还在耳畔迴响。一首常棣之诗,让鹡鸰意外地成为兄弟友于的象征。一群鹡鸰又叽叽喳喳地飞进李隆基的笔下,至今还活在《鹡鸰颂》这个法帖里面。
鹡鸰集体扎堆,现在已经难得一见。尽管我们的世界还没有沦落到蕾切尔描述的那么可怕:剧毒农药渗入土地的肌体,让春天变得死一般的沉寂,大地的生机都被死神紧紧地扼住……但是,在我的有生岁月里,鸟类数量呈下降的趋势是不争的事实。我童年的时候,村后的大枫树上有一个很大的鹊巢,喜鹊用高超的筑巢技巧将一些枯枝扎在树杈上,里面铺上温柔的茅草、树叶和羽毛,既稳实又舒服,随后的狂风暴雨对它都无可奈何。到了春天,喜鹊就以鹊巢为中心经营属于它们的美好时光。在民间,喜鹊是吉祥的鸟儿,它的巢是受人保护的。差不多从我十岁那年起,喜鹊就集体将我们村庄遗弃了,再也不见它们的踪影。答案你也许想得到,农民开始不顾一切地追求增产增收,化肥农药被大量使用,喜鹊想逃,但不知能逃到哪里去,它静静地躺在田野上,躺在树林里,嘴边有一丝血污。其实,寂静的春天离我们并不遥远。
我见过形单影只的鹡鸰,但一直没有躬逢它们的盛会。我不知道一千三百年前的那个秋天,飞进李隆基的深宫的那群鹡鸰是些什么颜色?我经常不期而遇的白鹡鸰,会是李隆基见过的那群鹡鸰久远的后裔之一吗?令人难以置信。毕竟生命薪火的传递比奥运圣火的传递要艰难得多,再说,一只可爱的鸟儿从来不曾伤害过一个人,但人总是有意无意地布下死亡的陷阱。
有网友撰文称,一个久雨初晴的日子,在办公楼的空地上,他亲眼目睹了二三十只白鹡鸰翔集的一幕。似乎可以佐证,白鹡鸰安于独处,也乐于群居。于是我又有一种错觉:当年逗停在麟德殿的鹡鸰,有一天会穿越时空出现在我面前。
编辑 陈冬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