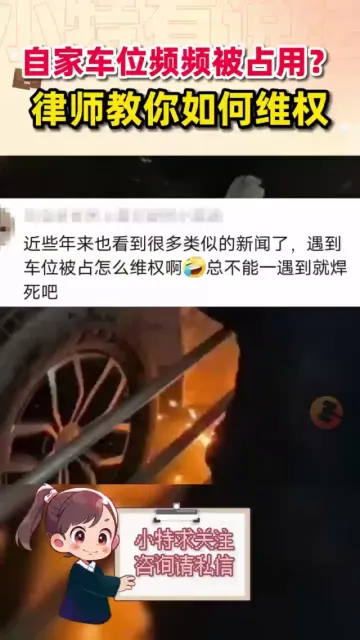小暑将至,江门新会正午的气温达到36摄氏度。
南坦葵林里,杨兰看着男工友将一捆三四十斤的葵叶搭在肩上,走到货车旁传给梯子上的兄弟,再传到车顶。叶子抖落的细屑被汗水打湿,粘在他们赤裸的背上。
这些葵叶不久后会被运到广州,做成扫把。

葵林里的工人。
货车百米外的拐角处,农民模特聂泽伦身穿红衣,撑着小船,从水道的这头划到那头,再回到这头。岸上十几个影友举着单反,对准他按下快门。
聂泽伦是本地人,年轻时也在这片葵林里干过杨兰的活,现在他65岁,选择以一种更“优雅”的方式出现在这里。
来自外省的杨兰不关心这些,她只知道,这些年葵扇不见了,大家都买塑料扫把,钱不好挣了。
模特
周末的早晨,聂泽伦骑着老式二六自行车,从马路对面的九龙里赶到葵林,今天有一群摄影爱好者跟他预约了拍摄。
7点这个时间是影友们定的,夏天日出早,那时候的阳光比较柔和,穿过葵叶照射下来,晕成一道光环。

聂泽伦踩着单车赶到南坦葵林。
作为一个“从业”20多年的“专业”模特,聂泽伦今天显然有备而来。红色上衣突出主角,黑色宽松裤子方便做动作,头戴藤编帽子更显农民气息,自行车两边的把手还挂着不少摆拍的道具。
葵影婆娑下,寂静的葵林能听得到鸟叫的回声。不久,从城区10公里外开车过来的影友们陆续抵达,让林间多了些人气。

摄影“发烧友”正在拍摄聂泽伦。受访者提供。
影友们也是“全副武装”。除了那些聂泽伦看不懂价钱的“长枪短炮”,几乎每个人都穿戴着渔夫帽、冰袖、长裤,又防晒又防蚊。
不远处的杨兰穿得也差不多,只是她没有冰袖,多套了一件长袖。里面的上衣湿了一半,隐约印出胸罩的形状。她不觉得尴尬,反正其他男工友都赤裸着上身。
这个时间,杨兰已经在葵林里干了1个多小时的活。南方的夏天酷热难耐,为了减少中午和下午的工作量,工友们相约四五点天蒙蒙亮的时候,就开始割葵。
大多数情况下,男工友手持用四五米长木棍接驳的镰刀,抬头割葵,眼睛被太阳晒得一直眯着。杨兰负责整理掉落下来的葵叶,每30片小葵叶或者每20片大葵叶为一捆,用草绳缠好,靠在树干边上,中午收工前再一并搬上车。

聂泽伦割下一片葵叶。
有影友提出想拍割葵的画面,聂泽伦便在自行车上翻出一把用布包着的镰刀。因为手边没有长木棍,他只好挑了一棵矮点的葵树,左手握住叶柄,右手镰刀轻轻一划,葵叶掉了下来。
拍完这个景,聂泽伦把割下来的葵叶靠在树干边上,准备转场。他知道,葵林里有一拨外地人正在割葵,等下就会把葵叶收走。
前人
聂泽伦不是这片葵林里的第一个模特。
大概20年前,第一次有摄影师邀请他拍照。当时同村还有两个人也在做模特,只是时过境迁,一个与世长辞,一个年事已高,只剩下他了。
这些年,聂泽伦根据影友的喜好,慢慢摸索出一些做模特的门道。拿什么道具,摆什么姿势,站着还是蹲着,笑还是不笑,他有一套拿捏的标准。渐渐地,他认识了不少当地摄影圈的“大神”,也成了不少获奖作品的主角。哪张作品出自哪位“大神”之手,现在挂在什么地方,他如数家珍。

《葵林晨曦》。
传播度最广的一张,是当地书画家、摄影家周学勤拍摄的《葵林晨曦》。两岸葵树参天,一条满载着葵叶的小船从远处荡来,清晨的阳光穿过葵林,金色在画面中漫开。而船上的人,正是聂泽伦。
“你别看现在葵林这么安静,以前不知道养活了多少人。”
聂泽伦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,和那时候成长起来的大多数新会人一样,他从小就跟着家里人制作葵制品。
南坦葵林有1500多亩,是新会唯一保存较完整,且具有上百年历史的连片生态葵林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,葵林由附近的群胜村和九龙里分片承包。每到夏天和年末,生产队所有队员都会集合到葵林里进行收割。
“这里全站满了人。”聂泽伦张开双臂比画了一下,表示范围之大。他当时所在的生产队有大概90个劳动力——分工和杨兰他们一样——男的负责割葵,女的负责捆葵。捆好的葵叶通过“人肉传送带”,从葵林深处传到船上,走水路送往今古洲的葵厂进行晾晒和加工。那艘船很大,能装几百捆葵叶,比聂泽伦现在用来拍照的大一倍。
在那个记工分的年代,割葵一天大概能领到五毛钱工资。聂泽伦家里有6个劳动力,一天能挣3块钱。每半年完成一次收割,家里会吃顿肉庆祝,聂泽伦记得,那时候猪肉每斤不到1块钱。
葵乡
杨兰从外地来新会20多年了,为了帮补孙子上学,年近花甲的她还坚持做这份粗重活。尽管称得上半个新会人,但杨兰并不知道,新会还有一个别称,叫葵乡。
新会种植蒲葵历史悠久,早在东晋时期,已经开始葵树种植和葵艺加工。清代乾隆至光绪末叶的两百多年间,新会葵艺的发展达到鼎盛,葵树种植面积最多时达到6万亩,年产葵扇达1.5亿柄,产品远销欧美及东南亚各国。

南坦葵林。
1952年,火画葵扇被国家列为特种工艺品,发展出花席、花篮、坐垫、牙签、通帽等十大类上千个花色品种。郭沫若曾赞誉:“清凉世界,出自手中。精逾鬼斧,巧夺天工。飞遍寰宇,压倒西风。”
在那个年代,新会几乎每家每户都能跟葵扯上点关系。读书的孩子在上学路上织葵辫,刚毕业找不到工作的青年在家织葵篮,不方便走动的老人在家里的缝纫机前缝制葵帽,是再平常不过的场景。新会本土作家明明曾经写道:“大街小巷都铺满了晾晒着的葵制品,人们在街上行走,脚下踩踏的就是一柄柄葵叶或制作好的葵衣、葵篷。”
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,随着电风扇和空调等现代家电的普及,新会葵业开始走下坡,许多葵艺传人被迫转行。1999年,新会最后一个国营葵艺厂倒闭。也正是在那段时间,聂泽伦一家分得了八分地,他离开了葵林,种起了新会柑。
葵,作为曾经的区域经济支柱,日渐式微。幸运的是,它从实用走向了精美,在文化艺术的赛道活了下来。
2008年,新会葵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葵艺的保护和传承被提上了当地政府的工作日程。兴建葵博园、开发葵林自然生态区、打造南坦湿地公园、创办新会葵乡传统工艺品经营中心、在学校开设葵艺培训班……去年,新会葵艺入选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保护实践案例。
聂泽伦认为,自己就是葵文化艺术的传播者。
未来
中午12点多,杨兰和工友终于把最后一捆葵叶垒到了车顶。监工拿着木棍,在沙地上写下“330”,这个上午收割了330捆葵叶。

监工拿着木棍在地上记录捆数。
上午的活暂告一段落,4个男工友赤裸着上身走进林间的水道,将身上的细屑连同汗水一起冲掉。
杨兰站在岸上看了一会儿,捡起一片葵叶当伞,走路回家。她住在七堡村,每天来回两趟葵林至少要两个小时。其他人住在九龙里和群胜村的出租屋里,开摩托车几分钟就能到。

杨兰。
葵林里倒数第二个走的是货车司机,新会人,刚刚在阴凉处边抽烟边看着大家干活。上车前他绕了车子一圈,检查葵叶绑得牢不牢,确保路上的颠簸不会让它们掉下来。车子启动时,车上的葵叶又抖落了些细屑。
聂泽伦也动身回家了,下午他要去柑园施肥。这几年新会陈皮的名片打响了,他的八分地一年能赚个万来块。
葵叶的买卖还有人在做。
一个外地人承包了南坦的葵树,但他不做葵扇,而是做成了工艺要求简单得多的扫把。杨兰就是他雇的工人。
南方的酷暑还要持续几个月,曾经几乎家家必备的葵扇已经难觅踪影。但在刚刚落下帷幕的上海中国花卉博览会上,有一件精美绝伦的葵艺作品《锦绣南粤》。那是一只葵制的孔雀,尾屏的每一片覆羽都烙有南粤著名建筑。
不久前,这件作品乘坐包车,从新会运到了广州,再到上海。
(应受访者要求,杨兰为化名。)
(原标题《南方特稿|葵林里的模特和货车上的扫把》)